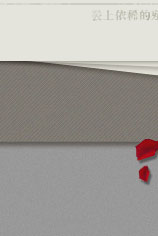在复旦网站上还找到这么一篇文章,希望yla喜欢
蒋昌建:昔日最佳辩手今日讷言为师 ■1993年的“最佳辩手”
■辩论在人生中可能只有一次,但是做人却是永恒的。
■辩论艺术是一个广大的宇空,我们只是在其中有限的一隅飞翔过。
■蒋昌建
■1965年生于厦门。
■1988年于安徽师范大学政教系毕业。后中学教书两年。
■1990年入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攻读硕士学位。
■1993年随复旦大学队首届国际大专辩论会折桂,获“最佳辩论员”称号。同年,获硕士学位。
■1997年,获博士学位。
■1998-1999年于美国耶鲁大学做博士后研究。
■现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讲师。

1993年8月29日,新华社发自新加坡:上海复旦大学代表队今天下午在此荣获第一届国际(中文)大专辩论会冠军。复旦大学蒋昌建同学被评为本届辩论会“最佳辩论员”。
当日辩题“人性本善”,复旦大学队以“反方”应对台湾大学队。
精彩的自由辩论结束后,复旦队四辩蒋昌建以高屋建瓴之势慷慨陈词,结尾一句“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要用它去寻找光明”,被评论为“犹如云层激发出雷电,把整场辩论升华到极高的价值观念境界,可谓气势磅礴”。
评委,美国哈佛大学杜维明教授在点评中赞扬复旦大学代表队配合默契,错落有致,引经据典,妙语连珠,体现了“流动的整体意识”。
新加坡《联合早报》评价“最佳辩手”蒋昌建:词锋锐利,反应敏捷。
“我自始至终以‘我代表复旦大学、代表前进中的中国’来为自己鼓劲。我要让新加坡人民和评委们看到,在中国,在中国的一所大学里,有这样一位学生,在这位学生身上感受到华语的优美和中国学生的知识水平。”赛后,当年的复旦国际政治系硕士三年级学生,28岁的蒋昌建如是说。
着手寻访蒋昌建之日,是8月荧屏上演“2000年全国大专辩论会”之时。网上聊天室里,有网友怅然地怀想“激动人心的1993年”,难忘新加坡首届国际大专辩论赛上辩手们的昔日荣光:“尤其那个蒋昌建,那时候我们模仿他的说话和表情,梦想有一天像他一样气势如虹。他影响了我们整整一批人。”
时间过去了7年。昔日队友有的做了中央台的节目主持人,在最近的采访里也还提及“我是做辩论出身的”,当年的经历依旧是身上的光芒。那么蒋昌建在哪儿呢,那个昔日最是风光无限的“最佳辩手”?
并没有过从高处跌落的感觉 8月23日下午1点,到上海复旦大学文科楼找蒋昌建。暑假里大学校园变成建筑工地最是理所当然。好不容易绕过地上横躺竖卧的午睡民工找到电梯入口,到6楼,国际政治系,35岁的蒋昌建是这里的一名讲师。
第一眼,认出蒋昌建靠的是他的眼神。印象中在7年前的照片上,他瘦得惊人,脊背挺得笔直,一身黑西服像是别人的,穿着实在不怎么好看。而眼前推门而入的这个人却是短裤凉鞋,一副走到大学生堆里就会被淹没掉的随意样子。唯一让人觉得不一般的东西在他的眼睛里,他抬眼凝视过来的时候,记者想起当年那场辩论赛的转播导演说过的一句话:“蒋昌建有一种气势,他人格里有一种从容,给人感觉似乎他要比他那瘦小的身体大上好几倍。”
还有他的声音。当年那场辩论赛的顾问王沪宁教授有一段回忆:“第一次到新加坡广播局试音的时候,我方几位队员简单地讲了几句话,为的是调试音量。蒋昌建一开口,他那特有的男中音和有魅力的嗓音,就吸引了大家。新加坡广播局的郭奕好小姐,就向我这里看,并伸出大拇指。意思是你们的队员不错。参加辩论赛,告诉我一个最生动的事实,那就是在复旦的校园里,在中国的土地上,我们有绝对优秀的学生,不比任何世界著名学府的学生差。”
当年曾让老师和复旦引以为傲的蒋昌建,现在做了复旦的一名老师,过着他自己说来是“与其他教书的和读书的人一样,简单得像白开水”的生活,而且不管别人如何惊奇和不解,安之若素。
“我现在这个状态跟你想像的有什么区别吗?”一见面,他就用一种很好听的语调问过来。记者说:“我曾经想过,什么是最该蒋昌建这样一个人干的事呢?至少应该是一个外交家,或者是一个在美国或香港能够存在的律师。”
他笑了,告诉记者其实做老师是他到复旦之日起就有的夙愿:“所谓从高处跌落的落差,在我这里,并不存在。我目前这种状态跟我内心所需求的东西比较兼容一点。什么是我的内心需求的东西?我要当教师,我要把我学的东西跟学生一起分享,我要有自由支配自己的时间,我要做一个,怎么讲,不是太紧张,有点闲适的人。我没有什么未来成就的愿望,因为对我来讲,我对自己的要求就是把书读好,书要教好,书要写好,能做这么一个‘三好生’我就不错了。
许多人问,你平时说话多吗?我很难回答,说了恐怕也会有人不信,我几乎除了上课,大部分的时间是沉默着的,因为,自己独处一间研究室,没人和你说话,如果真要发出什么声响,那可能我的脑子已经坏了。”
曾经的辉煌不大回想 一见面,记者就注意到蒋昌建身上穿的是一件“2000年全国大专辩论会”的T恤衫。他刚刚去做了其中一场的点评嘉宾。而去年’99国际大专辩论会在北京举行时,他的身份是美国耶鲁大学队的顾问。
事实上,从1993年那场“难忘的辩论”开始,与辩论赛有关的事情一直在他生活中留有痕迹。至今在他的办公室里,还堆着几大箱观众来信,他说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但是在他看来,7年前那次辉煌不过是“生活中一个偶然”:“一生当中你会有各种各样短暂的机会,你会迎接各种各样的挑战。代表中国的大学生去比赛,也许这挑战的难度、挑战的强度、包括挑战的密度,跟你一生当中遇到的各种各样挑战可能在形式上并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但是意义含量扩大了以后,你就特别容易记住这些挑战的事情。你说对我影响有没有,在我记忆当中它还算不算一件事情,当然算了。但是一幕幕的事情它过去了,我不大回想。
对于我来说,1993年辩论赛唯一值得我骄傲的是,我完成了一项任务。我喜欢这样的感觉,做一件事情,在大家对这个事情本身没有把握的时候,我会对某些比较重要的人物说,放心吧,我会把这件事情做好,那结果我完成任务了。我觉得那个时候我特别地愉悦,如果说有什么感觉,我就是这个感觉。我答应你把这个事情做好,结果,我做好了。
所认,我觉得它对我的影响谈不上有非常大的,不构成一个非常严重的影响,特别是改变你的生活,或者改变你的读书、学习、教书的习惯。没构成,对我没构成。可能对关心我的人,他们对我的印象会有影响。比如说他们经常定位成你是一个专门搞辩论比赛的,专门是参加辩论活动的,或者是专门从事这种论辩演讲行业的。这个影响可能在他们对我的印象上。但这个是没有办法克服的,因为你教学的一面,你读书的一面,跟所有的普通人其实都一样,很多的媒体它关注的不是你这一面,所以它报道的大多数都是你在这个辩论和演讲的场合所出现的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公众很容易地去有这样一个印象。
所以最大的影响是在这边。不过我自己倒不是特别地在意这个,我不是说躲起来呀,有这样类似的活动我不参加呀,因为没有必要这样去躲啊藏啊,或者去避开这样的活动。因为这样的活动一年也发生不了几次,一次也发生不了一个礼拜或者10天,你说平时挤时间怎么挤也就出来了,用不着去像挤海绵似的,用不着什么‘别人喝咖啡的时间’,那些都用不着。所以大部分的时间我就是一个教书的人,在做一般老师所能做的事情。”
辩论赛创造了一种文化 而今的蒋昌建,是大学里一个上课不看讲稿、喜欢在教室走来走去并时不时讲得兴起就坐到桌子上去的老师。一位去年毕业的听过他课的复旦女生,至今仍然在谈到他时眼睛发亮。她告诉记者,蒋昌建是复旦受学生欢迎的老师。
蒋昌建也显然比较满意他与学生的沟通,但是同时他还有另一分警觉:“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学生是因为我名声在外选我的课呢,还是真的觉得我的课好。”
在他看来,他在辩论赛表现出来人们认为是才华的东西并不完全属于他自己:“可能在一瞬间,我凝聚了某些才华的东西,但这个才华的东西不是我一个人的,是一个集体,甚至它不是一个小集体,它是一个大集体,它可能包括复旦整个教育的体制凝聚在这里。它不代表个人,我一直觉得不代表个人。
所以我跟学生们说,你们如果看到这个比赛之后有这样一个印象,你们来复旦这就对了,但是你们如果说在重复着我进行的那些学习方法、工作方法,可能你们得到的东西不会很多。但是如果你把你们想要学的东西、想要在复旦追求的东西,同复旦整个教育体制能够很好地结合起来,充分利用复旦的资源,你可能做得比我还好。
我觉得就是这样一个问题,所以我经常跟同学们说,不要有一个错觉,就是说好像你不主动地跟这个体制靠拢,你不主动去挖掘复旦的资源,你只要到复旦来,好像跟昌建一样到复旦来,坐到那个教室里,同样三点一线地过日子,你就觉得肯定能够成就,那不一定。”
跟许多人不同,对于现在辩论赛的风光不再,蒋昌建显得没有那么失望:“为什么要问辩论赛还会不会有春天?它从来就没有到过秋天,我们那时候是过热。辩论赛的意义不在于比赛,它创造了一个大胆讨论问题和表现自己的文化。
而这样一个大胆讨论问题和表现自己的文化,长期以来可能是被压抑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不主张你多发言的,所谓‘讷言敏行’,但在市场经济的社会里面,当人力变成资源的时候,说话变得特别重要起来,你怎么样在短时间内在人力资源的市场当中把自己推销出去。这完全是靠语言的功夫,这点有它的实用性在里面。再往上面讲就是你大胆地讨论问题、大胆地表现自己,这是这个社会越来越开放的一个缩影。”
本文原载于2000年9月6日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