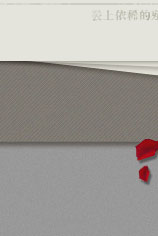短暂的城市2009-04-19 13:17:29
扬州:短暂的城市之一
把“短暂”修饰在这座著名的城市面前,肯定引起很多扬州人的不满。他们探帻索隐,把曾用文字记载下来,留在典籍里的扬州全都翻检出来,好厚的一部扬州史!不过,严格地说,这多半是书籍的回忆,而只有满清之后的段落归属于他们自己。此前,江南轻梦,二十四桥,骑鹤而下……当那些传说中的晶体绽放并枯萎的时候,他们的先人离扬州的距离,跟我离扬州一样遥远。
我在扬州住了很短的三年。曾令我很不能习惯的是,每一天,城市里的公交车在晚上七点准时全体失踪,随后,整个城市睡去,直到东方大白——演绎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古老故事。剩下一些不眠的街灯,安安静静地,不知为了什么而亮着。如果这个时候去瘦西湖外走一遭:古式样的园门,依稀可辨的楹联,灰暗的飞檐和廊柱。扬州或许唯有在此时此地,才象无边无际的夜色一样,充分地弥合成一整个古城。夜色中瘦西湖的湖水,映出白色的月和清朗的风。远处,园林里的某处树枝间或小岛上,一只大禽突然被自己的梦呓惊醒;此起彼落的鸟群,在随后几声尖利而凄清的高鸣之后又失去了动静。那时,我想到了比现实中更为悠长的一个扬州:人空空,建筑上的雕饰灰暗,野草在黑夜里生长……但那只是我刹那之间的想象。
最好不要再在白天光临同一个瘦西湖的大门。那儿会冒出大量的奇怪动物,它们纷纷披着长长的绒毛,色彩光鲜,在太阳下拥挤在一个个鳞次栉比的地摊上,其密度远超过城市里任何一部公交车。我和一位见多识广的湖南友人,管这些昼出夜伏、不可名状的长毛绒玩具叫做“妖怪”。在细节不乏可爱的妖怪们旁边,是瘦西湖畔的杨柳。而湖面上,饰有金龙盘柱的大汽轮,自我标榜是乾隆下江南的御船,从御码头开出,正在用轰鸣的马达和翻滚的浪涛招徕游客——他们认为乾隆是个聋子么?
我不知道这些景象是否会进入扬州将来的记忆,好在记忆总是会挂一而漏万的。也好在轰鸣的龙船只是偶而在瘦西湖上一现神威——要不然的话,我一定无缘听到夜鸟的声音了——那是每年的四五月间,扬州城的每一个角落都用同一个短语包装起来:烟花三月。每年这个时候,扬州人民似乎都舍下他们的日常起居,匆匆装点起扬州的所有名胜,进而装点匆匆来去的各地游客的眼珠。转而游客四散,扬州城里所有的桃花一齐凋谢,一个暂时的扬州便留待明年再来。据扬州的出租司机说,他们在烟花三月里接待的游客,占到全年的大半份额。年复一年,在此外的日子里,扬州只留在散向各地的游客的记忆和照相簿中,偶尔再被打开一回。在此外的日子,如果没有去面对那些乏人问津的扬州名胜,几乎便可以觉得是在另一座随便什么名字的城市里生活。短暂的城市就是这样为短暂的旅游、为过客而建立起来的。
扬州的名胜多半也掺杂的外地口音,就象春天里光临它的游客。这让人疑心它们更象是一时方便的绰号:“瘦西湖”借来杭州西子之荣光,“小金山”则盗走江对岸镇江金山的盛名。用与远方景象来命名自身,实际上正是短暂的城市独有的美学。这是一个提供给外来者观光的地方:一些外地人(就像我这样),在清朝是皖南的盐商,在隋唐是南下的炀帝和杜牧,把他处的繁华在这里演上一遍。来自不同地方的人声一起在这里喧哗,这里便超越了任何其他所在。但是,外地的口音总会勾起对他处的回忆。曲终人散,外来者总会离开这座城市。他们反反复复地来去,给这里留下的,只是一座空城。清代的苏州人沈三白,把这种“人去也空空落落”的景象称之为“浮生”,漂浮不定是短暂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城市与人生的繁华就象是梦一般的不确定和不长久,在恍然间醒了过来,留下更悠长的只是一些遐思。
对了,“梦”从来就是扬州美学的首席关键词。诗人杜牧甚至还以梦为单位,精确地计算过这“短暂”的时间上限:十年。而它的下限,也在唐代被测定,小说家李公佐作为布景的那棵槐树今天还活在扬州驼岭巷,他提到,那个南柯梦至多做了半天——太阳还没有落山,太守就醒了。
也许,比诗人和小说家更标榜准确的学者们,可以找到一个曾经长治久安的扬州来反驳我。且不用去管他们枯燥和败兴的话语。有很多短暂的瞬间,是他们到今天也无法替扬州回忆起来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万里之外写道,他已经把欧洲的荣耀镌刻在大元帝国最繁华的都市历史上了。据马可说,他在“扬州总管”任上逗留的时间,跟我一样,整整三年。但迄今为止,没有人在扬州找到马可·波罗的任何旧迹。有人因此开始怀疑他的忠实,但虔诚的意大利人可能不会。同样为了这一段话,前些年他们给扬州送来了一头铜铸带翼的狮子。我曾经在扬州天宁寺的院子里短暂地见过它,那个与“圣马可”相关的家伙也许是在来东方的旅途中,与中亚草原上的骆驼和风沙厮混得久了,高而瘦,用古怪的神情在中式庭院里仰望着天空。但是它终将盯着大殿内的天花板,度过更为漫长的日子——门票昂贵的博物馆把它请进了室内,我便再也没能见到它。
意大利狮子跟我们那种象看门狗一样豢养在大门口、习惯于在节日里摇头晃脑、大撒其娇的狮子几乎就是两种动物。只要见过它一面,便很难把它忘怀。这意味着短暂与深刻并不矛盾。扬州博物馆设在天宁寺的大殿,天宁寺是曹雪芹的祖父曹寅组织人马编撰和刻印《全唐诗》的地方。天宁寺与普通扬州市民日常生活的关系在于,这里的院子是书画、折扇、古董、电话卡和旧书的批发和交易市场。从小巷深处拆下来、挖出来的清代扬州的碎片,一部分便被送到了这里,一部分被送进大殿。在原先大片大片扬州小巷的地方,一幢幢水泥的高大建筑物正在建造中。
那是前年我离开扬州时的景象。那些建筑物一定早就封顶,装潢一新了。那是另一个貌似更为稳固的扬州正在迅速地萌生出来。扬州本不通火车和飞机——这也终于掩入历史:铁轨正从南京方向迅速游动过来,在古代诗人吟唱过“春风又绿江南岸”的瓜洲古渡附近的长江江面上,一座建设中的大桥也终将这座城市和它向往的江南联系起来。“润扬”,大桥的名字本出于阿谀,但同时也富有拯救的深意。
改动意味着可以改动,拆除意味着应该拆除、拯救意味着需要拯救,湿润则意味着原初的干旱。短暂的扬州就这样,在意识深处成为一个龟裂的、散落的与颓败的城市,而正在变得更为短暂。企图取代它的,一个自足而现代化的城市,却与其他城市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届时,我去扬州,或许只能从投往瘦西湖的一瞥,从那一刹那间,回到这个短暂的城市。
http://www.douban.com/note/314918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