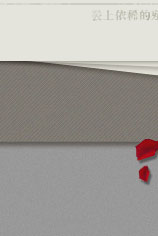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许知远
2007年6月7日 星期四
那
几个少年依旧手不释卷,神情专注,他们的脸上则罩着氧气罩。“遂宁一中即将参加高考的学生正在市人民医院高压氧仓一边吸氧一边复习”,照片下附带了这则说明。关于高考的新闻,像股市消息一样占据着过去几周的媒体。今年是高考恢复30周年,同时参加高考的学生创纪录的达到了950万。空气了充斥着高考的味道,那些过来人开始不胜感慨——高考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而这一年的考生来讲,紧张感日益增强,尽管中国大学的声誉正跌入谷底,但这不影响每个家长仍将子女拼命送入其中,心甘情愿的承担昂贵的学费,然后再为毕业后的子女找工作、买房子赔上所有的积蓄与心血。我们的社会更富裕了,技术更先进了,程序更规范了,但个人却似乎变得更脆弱了,以至于只对病人使用的氧气罩都被使用在这些18岁的年轻人身上,家长们则担心明天的交通是否堵塞,考场是否合适,那家餐厅提供的营养餐是否真的有营养,甚至商店里2B铅笔都被一抢而空。而这些年轻人仅仅是去参加一场考试,如果一场战争到来,他们该怎么办?
我知道这种感慨可能招致的愤怒。对于这950万人中大多数来说,他们会同意福建省武平县第一中学的那位叫王锦春老师的话:“铁路?没有。高速公路?现在还没有。要资源,没什么资源。所以对我们武平人来说,只有一条路,就是通过高考这座独木桥,考出去,离开这个地方。”中国人总是在为基本的生存资源而奋斗,像很多年前一样,考试是维持社会流动的最重要的工具。
在年轻导演周浩的令人动容的纪录片《高三》中,我看着那些堆积如山的卷子与课本,那些大声的背诵历史书的幼稚面孔,还有那个因为压力太大而喝醉的少年,突然想起了南京的科举的旧考场。一直到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前,一个男孩子(那时女孩子不用考试,却要裹足和刺绣,不知是喜是忧)为了应付科举考试,要从7岁开始学习,大约要以6年的时间记诵四书五经,共43.1万字,要熟记8000到1.2万个常用字,他每天平均要记住200个汉字,考生还要勤于毛笔书法,参加每3年举行的一次乡试。经过5天考试,很多“笨孩子”就被淘汰了。考上的人就有资格参加会试,每期三天,最后才可能参加廷试。廷试不仅需要你写一手文章,还要你锻炼控制身体的能力,因为在连续几天的考试中,每天只能上一次厕所……
科举是中国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它的遗产是复杂的。一方面它稳固了政治统治,它将这个社会最聪明、雄心勃勃的年轻人容纳一个价值体系中,即使你考取了最低级的秀才,在你的乡村,即使最富有的人也要敬你三分,他们穿着长衫,即使犯了错误,县官的板子也不能打他们,他们的特权激励了更年轻一代同样加入这场考试;它也带来了社会的流动性,“一举成名天下知”和“富不过三代”的古老说法一样,说明中国没有自己的贵族传统,也没有力量可以和皇权相抗衡,社会被分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一部分,皇帝统治者具有绝对的权威性和连续性,而从最高的官员宰相到一个普通人,他们的地位都是不稳固,随时可以对调的,这样就没人能挑战统治者。对于一个牛车耕地、步行的社会,这样的制度优越性一目了然,它给普通人提供了某种希望与公正——政治家最需要提供的两样东西。但它也毒化了一代代“最聪明的头脑”,考试窒息了他们的好奇心,他们可以写出漂亮的八股文章,却发明不出蒸汽机,也创造不了进化论……当英国的舰队在中国的海岸线出现时,这些饱读诗书的人束手无策。科举考试可以维持一个相对静态的社会,却无力对抗动荡的新世界。我丝毫不怀疑,科举制度同样造就了一些伟大人物,晚清最后的状元张蹇不也可以摇身变为实业家和社会领袖,但这是多么偶尔的产物。决定教育制度优劣与否的是它对于普通个体的培养,和为一代代人提供的持续性的提升。
1977年恢复的高考,像是1905年科举制度的回响。它给当时的中国社会提供了上面提及的两样最渴望的东西——希望与公正。但是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这个制度已经处于破产的边缘。在很大程度上,高考就像是中国社会的缩影,人们陷入了低水准却高强度的竞争。人人都知道,那些死记硬背、没完没了的应试只会让年轻人失去对知识的热忱,这还助长了社会已经浓烈的了机会主义心态,以为只要度过这一关就万事大吉。而且,我们已经看到了,经过这重重考试进入大学的年轻人,在四年教育之后,常常既没有被获得灵魂上的解放,视野上的开阔,也没有获得基本的生存技能。于是,一个悖论出现了。我们是个一个资源匮乏的社会,大多数人渴望通过考试来获得多一点的生存空间,但教育却成为我们社会最大的资源浪费——那些毫无价值的复习材料浪费了我们多少树木,那些毫无意义的焦虑的夜晚伤害了多少年轻人的创造力,那些建造了无数高楼大厦的大学却既没有杰出的学术也没有伟大的心灵……
不要以为这一切都不能改变,就像人们总在感慨中国的事情是积重难返。让我们想想1905年之后的中国教育界发生了什么,科举制度废除了,但私人创办的学堂却迅速兴起,在不到两代人的世界里,新一代人创造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的黄金时代,出现了蔡元培、梅贻琦、张伯苓这样的大学校长,孕育了傅斯年、钱学森、杨振宁这样的新式的大学毕业生。中国人的能量是惊人,只要他们被纳入了一个正常的轨道。
今天的我们面临着新的情况,社会的流动性使的高等教育变成了每个中国人都要尝试的消费品,多年来把压抑的情绪释放出来了,人们像购买彩电、冰箱一样,让自己的子女获得大学学位。但正是在此刻,教育的分层和多元化变得至关重要。精英教育要变得真正精英,它就是为了培养未来的领导人而存在,而职业教育则更职业,它为我们社会输送源源不断的技术人才,它们是不同的路径,通往不同的方向,却都是今日的中国社会迫切需要的。就像我们面临的灾难性的环境问题一样,政府也必须意识到他们同样难以应对教育的挑战,除非让更多的民间机构公平的享有提供教育的权力。如果张伯苓那一代中国人可以在一个世纪前,依靠社会力量创造教育的奇迹,今天的我们同样可能。只有到那个时刻,高考生那些毫无意义的夜晚,才可能真正不再重演……
(作者的邮件
edmund.z.xu@gmail.com,他最近的一本书是《我要成为世界的一部分》)
《2007:中国纪事》